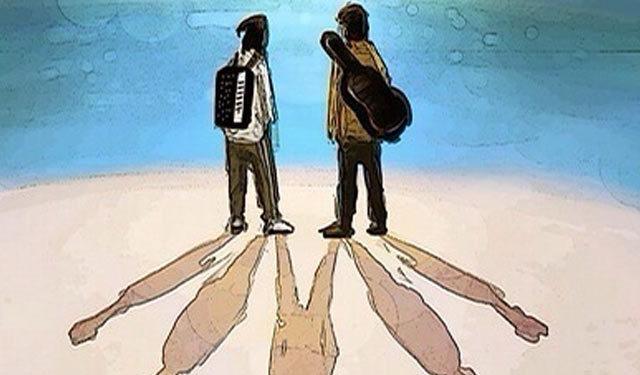:: 建议点击来源链接阅读、收听或观看 ::
几年前,有个好朋友说了一句口号——“民谣接过了摇滚的枪”,那意思大概是如今民谣比摇滚更劲。
也不妨接着说:后摇接过了摇滚的枪。但这种修辞方式就跟说“散文接过了小说的枪”一样奇怪。我不是说摇滚就有多劲,只是接过这杆红缨枪的也可能是空心人,民谣热或后摇热,同样容易陷入审美的惰性和表达的陷阱。
民谣容易变成一个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柔软的沙发,人们深陷其中,左搂右抱两个风情万种的情妇,一个叫乡愁,一个叫诗歌,并且时不时捡起底层的烟头,吹出几个正义的圆圈。我当然不是在说乡愁、诗歌以及底层情怀的坏话,只是说它们坏就坏在、死就死在泛滥而拙劣的表达上。
乡愁的大好时光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以海子之死为圆心。而国内民谣则以野孩子乐队以及赵氏兄弟(赵已然、赵牧阳)为极致,乡土成长记忆和1990年代的北京商业社会冷酷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成就了他们的乡愁挽歌。
人的《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则是下一个时代与西北遥相对应的南方乡愁挽歌。对五条人乐队最经典的评价,一个是“音乐的侯孝贤电影”,另一个则来自《南方周末》的颁奖词,说他们“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这两个评价本来针对的只是五条人第一张专辑《县城记》,但至今一直像招贴一样贴在他们身上。实际上从第二张专辑《一些风景》再到第三张专辑《广东姑娘》,他们已经撕掉了旧招贴。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问题是十年工夫水没准就又流干了。我的意思是:信息、通讯和交通的加速流动,人在远方与本土之间、在现实与虚拟空间之间的加速流动,都足以把乡愁压缩成压缩饼干。

我2008年第一次去台湾,坐捷运列车时,眼前首先掠过侯孝贤早期电影的镜头:南部的少年背井离乡去台北打拼,乡愁像铁轨一样漫长。然而如今火车实在太快了,用陈升的话来说:“便当都还没吃完就到了。”广州和海丰之间如今高铁也才一个多小时。正如左小祖咒在《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歌中所唱:“信息反复收到,我在帮你订票,速度高于一切,要尽快做出成绩。”
于是,我们不得不开动乡愁割草机,一茬接一茬地收割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乡愁,民谣与其说是在种树种草种地,不如说是在制造新式乡愁割草机。但脚下的土地,可能已经连一台割草机都容不下。面对“脚下的土地与人”,谁说一定要吟咏不可?莫非那儿有个贝加尔湖?有时候文艺乡愁防腐剂反而污染了土地,土地并不仅仅只是抒情的对象和乡愁的载体,它还是政治经济革命与改革的焦点,社会历史权力斗争的场域。在《曹操你别怕》这样的歌中,五条人扼住了吟咏的喉咙,发出了奇怪的声音,这在中国当代民谣史上,是理应被吊销民谣执照的事,他们简直是拿民谣来打架了,这首贫穷朋克民谣作品,是县城烂仔对海陆丰令人闻风丧胆的农村械斗传统和红色政权阶级斗争历史的追忆和挪用,也是乡村戏曲传统和现实生活的互渗——戏曲(海丰有白字戏正字戏)是族群和宗族团结的粘合剂,甚至也是暴力冲突后赔礼与和解的仪式。曹操与彭湃一起穿越,为县城烂仔护驾。

今年(2015年)大年初三,五条人一年一度的“回到海丰”春节演唱会,终于第一次有了像样的场地来搭台唱戏。那一小块只能容纳六七百人的空地居然号称“方太广场”,据说属于旁边的方太厨具公司——五条人有一年春节演唱会没地方搞,居然是在该公司的办公室搞的。这个所谓广场紧挨着高速公路,紧邻一家叫“第五大道”的KTV,和一家叫“巴黎香榭”的SPA,怪不得五条人在《做梦》一歌的视频,敢反转政府口号,变成——“立足世界,放眼海丰”。这个所谓广场是产权不明的,据说曾差点酿出农民和县城烂仔的一场火并,这是去中心的无厘头的一块飞地,五条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仅仅存活一天的“县城坎普”革命政权,以及“山寨全球化”群众艺术中心。《曹操你别怕》引领那些韩流日系发型的县城靓仔,为千百年纷争不断的土地,举行了一个摇滚洗礼。

民谣往往是通过对脚下的土地的吟咏,来获得一种追昔抚今、千年同心的“超稳定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南方周末》表扬他们“舒展了原汁原味的乡野中国”乃至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然而五条人直面的是一片早已分崩离析的动荡不安的土地。在《海风》一歌中,他们曾经提及几十公里以外的乌坎,一个新时代土地问题的火山口。新专辑再一次用了这首歌,但这一次把乌坎删掉了,那倒不是因为敏感,而是为了超出地域和时事,表达出中国的县城青少年共通的相似的成长经验——“带我离开这个县城”,出走,似乎显得比回家更焦灼更迫切。五条人的《广东姑娘》新专辑更多的是广州生活经验的产物,或者说,他们把“乡愁”的时空拓展了——从海丰到广东,并重返八九十年代,那个属于歌舞厅和录像厅的青葱岁月。
这是反民谣的民谣,他们对民谣双面夹击,一面是朋克风骨、戏曲腔调,乃至街头烂仔的撒泼吵架,一面则是不惜将自己调低到口水歌的档次。这正是这张新唱片的有趣之处:一方面好多旋律甜的都快得糖尿病了——《广东姑娘》就像是张学友刘德华的歌——而这种流行口水歌的调调和刻意做旧的音色,和他们的好基友“顶楼的马戏团”那张《上海市流行金曲十三首》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又尽量摒弃文艺腔调,尽量摒弃修辞修饰,尽管我并不算《走鬼》这样的歌的拥趸,但不得不承认只有这样直白到白痴地步的歌词,才足以表现“城管打人”的题材:“他是个画画的他是个画画的,你打断他的手筋还怎么画呢?”作为文艺走鬼,五条人扒光了民谣的文艺外衣。但最直白的语言也可以充满诗意,比如,说唱怨曲《心肝痛》最后才冒出一句小学生作文的比喻:“生活应该像海里的鱼”;比如《晚上好,春天小姐》那句“市长先生已经把你遗忘了吗?他曾对你说:这儿永远爱你”,这不是市长包二奶的新闻联播;又比如:“你看那风,有时往东吹,有时往西吹,我的头发就是这样吹乱的啊”,这是诗意,不是诗遇上歌。
资深文青惯于从文艺去发现文艺,而不是从生活发现文艺。不少人都说五条人模仿了左小祖咒的唱腔,有位高级文艺犯甚至指出《像将军一样喝酒》模仿了左小祖咒的三种唱腔,三种!不错,左小祖咒、盘古、胡吗个……他们的外地口音,他们胆大包天的破嗓子,都指引过包括五条人在内的后辈。但一个完全不知左小为何物摇滚为何物的县城阿三可能更清楚:阿茂的腔调,更多的来自传统戏曲(海丰白字戏及其民间变种)的耳濡目染,来自南蛮野种的日常说话方式,来自边缘社会那股呛人的骚味,其吵闹和难听,不是刻意为之的模仿秀,而就是如此,只能如此,不得不如此。
我曾有文论及五条人前两张专辑,名为《豪猪与走鬼》。结果他们新专辑来了首《走鬼》,又来了首《猪母上山咬老虎》,猪在五条人的作品中就像在库斯图里卡电影中一样是个狠角色。与其说这是底层情结,还不如说是喷涌而出的地气,这股地气不用接,接也接不住,因为它一直在狂喷。
人《县城记》讲述的也已是多年前的县城了,如今的海丰俨然是一个紧随高速公路和高铁大肆扩张的城市,唯有东门头倒港币的表叔公还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坐成时代的雕像,唯有陈炯明都督府院子里四处乱丢的被县城烂仔用作软性毒品的咳嗽药瓶子——尽管当年陈炯明曾大张旗鼓地禁毒禁赌——提醒我们,任何时代都有无处宣泄的青少年荷尔蒙有待喷涌。“踏架单车牵头猪”的少年往事一去不复返,那是一个“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的时代 。海丰的一大象征是NEXI,也就是三轮车的TAXI,NE是海丰话“踏”之意,NEXI与TAXI押韵,NEXI犹如乡野游击队,在TAXI和公共汽车之间穿行,破坏着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则,给城市带来危险,以及乱哄哄的活力,而五条人就像是一辆风驰电掣的NEXI。

但他们还是民谣吗?还能领到民谣的资格证吗?NEXI早就从脚踏三轮车变成电动三轮车了,但当地人依旧叫它NEXI,你愿意继续称五条人为民谣也没问题。在这里,民谣与其说是一种音乐类型,还不如说是一种气质,一种视角和姿态,它绝不高于生活,不做出艺术高于生活的姿态,它是平视的,平行的,它和民谣中的“民”共生。“民”似乎应该解释“普通民众”,但重要的不是大而化之的“民众”,而是在众人之中发现那特别的一个,在一个普通人中发现他或她并不普通的光彩。我的朋友、历史学家胡文辉在新书《反读书记》中有一句话触动了我,他坦承他自己不过是个乐得看热闹的“小市民”,他并没有摆出一副“你们为何要娱乐至死?为什么不愤怒不批判不反抗?”的姿态。这令我想到五条人那首反乌托邦红歌《彭阿湃》,歌中描述彭湃被捕时,那些上海的市民说:“我不知道呀,我在看戏。”但请注意,五条人并没有对冷漠看客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也是在看戏,既看英雄也看草民,在角落里,反而看得见更多的好戏。或许,这才是民谣精神的正解:以“流传”去战胜“流行”,歌唱在戏梦中流传的人生。
正如杨波指出的:民不民谣并不重要。若只是作为音乐类型,民不民谣确实不重要,五条人当然也变本加厉地从民谣穿肠而过,继续大摇大摆张牙舞爪,在《像将军那样喝酒》中他们再次扮演了贫穷朋克,在《心肝痛》中玩转了方言Rap,在《龙哥有真爱》和《走鬼》则干脆唾沫横飞地讲起了古仔,而长达十分钟的《请到老祖公》,天呐,那是自由即兴迷幻摇滚的天外飞仙。至于专辑的另一半,则是粤式流行金曲的甜点。
这是一张令民谣四分五裂的唱片,五条人是民谣突变体,甚至是民谣粉碎机。我希望通过阐述这样一支特别的民谣乐队,部分回答关于“民谣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无非是入地上天——入地务求把根牢牢抓紧,上天何妨飞到天边外,无非是在天地之间制造分裂,在分裂中前行。五条人有一首老歌叫《清明过纸》,而在迷幻得飞起的新作《请到老祖公》中,清明祭祖与时俱进,纸做的电视空调都属于旧货色了,如今清明过纸悍然出现了纸做的iPad!乡愁还是一枚窄窄的邮票吗?急剧压缩的时空令土地与人的关系严重失衡失重,但也正因如此而获得了另一种魔幻的激情,一种穿越的张力,就这样用iPad请到老祖公,就这样重返未来。